葛兆光:從一幅古地圖展開的全球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圍繞一張古代地圖的講解,能否吸引聽眾的足夠興趣,撐起至少一個半小時的公眾演講時間?早前的香港書展,知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的演講「一幅古地圖中的全球史故事」,應該說實現了這一點。
演講當天,會場的數百個座位坐得滿滿當當。記者所見,這是整個書展期間除學者李歐梵與許子東對談張愛玲、也許還有作家龍應台談台東生活之外,聽眾最多的演講之一。當主持人提問聽眾來源時,不僅有本地市民,還有一多半讀者舉手示意來自內地。
在之後的訪問中,葛兆光繼續侃侃而談,從中國史研究說到全球史的視角,再聊到東南亞及香港史的研究情況。在他看來,海洋會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向,而重視海洋,無法迴避香港。

一位早年從事古典文獻研究、以中國思想史寫作聞名的學者,何以有如此號召力?一方面,應歸功於他1980、1990年代所寫的多部傳統文化普及學術著作,在傳統教育和文化聯繫被硬生生割斷數十年後,客觀上起到了幫助當時如飢似渴的內地讀者補充知識、賡續文脈的作用;另一方面,亦與他是文革後成長起來一代學者中的表表者,20多年前即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在香港有多年生活經歷有關。是以,本港讀書人對這位壯年成名的葛教授並不陌生。
不過,能以一個看似不動聲色的冷靜題目,吸引眾多讀者坐到最後,亦顯現出題目本身所展現的想像力,以及葛教授的清澈口才和開闊博學的國際視野。演講結束後買書等候簽名的聽眾長龍,從台前一直列隊到了最後一排轉角。
也許葛教授早有預料,此前他已把採訪時間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休整一晚後,年已75歲的葛先生,着一身白色棉麻短袖長褲,身板挺直,施施然準時而至。置書展方備好的長條沙發於不顧,他隨手拉過座椅輕鬆坐下,像是一位和善、好脾氣的飽學宿儒,又要開始擺龍門陣了。
「中國史已經不能封閉起來寫了」
由古地圖展開的研究思路,20年前葛兆光於美國訪學時已演講過。不過,作為研究對象的古地圖早有變化,此次被列入演講主題的古地圖,是一幅藏於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公元1402年由朝鮮人參考中國疆理圖繪製而成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在葛兆光不疾不徐、抽絲剝繭的介紹下,這幅地圖的發現意義,不僅展現了13至14世紀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也展露出今天還只能靠考古、實物發現等方式,才能了解到的中世紀知識的全球傳播狀況。

「很多人在理解歷史時,只把歷史看成是個別國家內部的事,實際上不是這樣。你看這個地圖就囊括了阿拉伯和波斯的知識,也記載了歐洲的知識。然後它傳到了蒙古人那裏,蒙古人傳到了漢族人,漢族人又傳給了朝鮮人,朝鮮人的這幅地圖又傳到了日本。」
從古地圖繪製折射出的知識傳播演化,進入對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研究,正呈現出葛兆光數十年學術趣味的演變。從他成名作《中國思想史》的副標題「中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已可略微窺見他學術生涯的思考方向。他由早年的古典文獻訓練出發,進入宗教研究,再到思想和文化史,最後到世界史,反映了一個有濃厚中國問題意識的學者,從本土再到世界文明版圖中尋找解決之道的求問之徑,「知識交流和全球聯繫,是其中的重點」。
2000年秋,在清華大學執教的葛兆光,以7年時間完成兩卷本大作《中國思想史》,當他準備第三卷1895年後的思想史寫作時,已意識到此後的中國史「已經完全不能封閉起來寫了」,因為「中國不再是一個獨立、孤立的中國,已被整編到整個世界的大歷史裏去了。任何變化都跟外面有關係,這就迫使我們要關注外域,關注周邊。」
到此已可解答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疑問——為何會從古地圖入題?「古地圖是個小事,但它背後體現了一些古代中國對當時世界和中國的認知,然後再想這些認知對今天中國人有何影響。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古地圖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思想史的材料。」葛兆光說,「回過頭來看,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知識已有了全球交流聯繫的過程,這使得我們要改變過去以國來劃分人民的觀念,這恰恰是全球史研究要做的事。」
從兩個範例看全球史研究
2006年,葛兆光辭去14年清華教職,南下上海出任新成立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籌建研究院之初,葛兆光就定下了「從周邊看中國」、「域外所藏有關中國的圖像資料」等研究方向。「人的眼光都是不斷放大的,1980年代以後我們歷史學家的眼光也同樣在放大。我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就中國談中國,反而講不清楚中國。沒有對照、沒有鏡子的話,很難清楚地認識自己。」為說明這一觀點,他介紹了兩個看似毫不相關、但在全球史演化中緊密相關的例子:一個是發生在7世紀的朝鮮半島,有中國、日本、朝鮮等多方參與的白村江之戰;一個是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事件。
「這場戰爭對中國來說不重要,在《新唐書》、《舊唐書》裏都只有幾句話。可是對朝鮮人來說,這事太大了,因為新羅要取得唐朝的支持,就必須大唐化,採用唐朝的衣服、唐朝的官制、唐朝的文化,最後導致整個朝鮮半島的歷史轉向。而對日本來說,因為戰敗了,改革就只能完成一半。為什麼?因為日本各個地方貴族的軍隊都損失掉了,只得維持貴族的地位,讓各個貴族繼續佔有地盤,這樣中央集權就不能徹底。日本後來的走向,就跟中國不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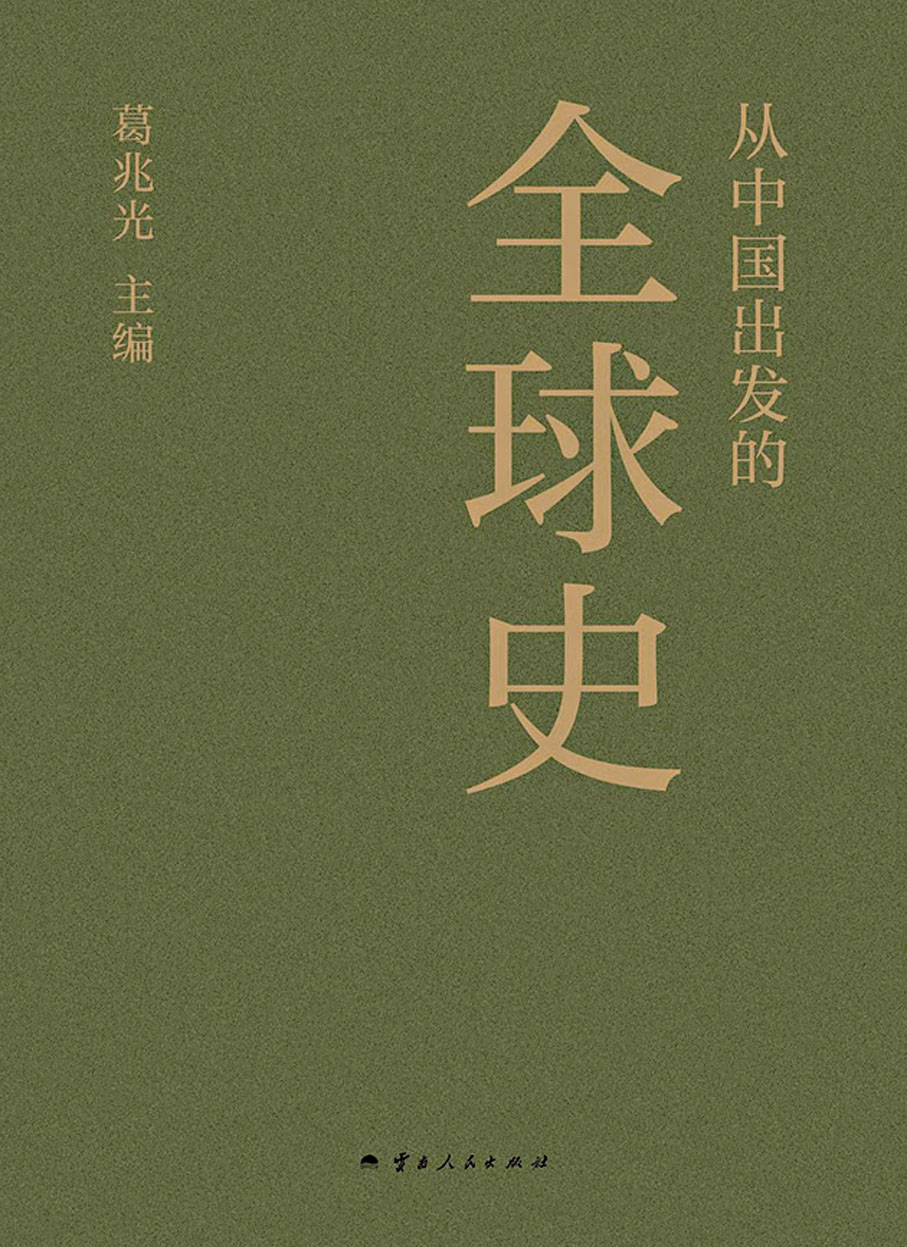
「所以放在亞洲環境下看,白村江之戰變得很重要。」對日韓相關文獻有研究的葛兆光介紹,「在日本,一提起白村江之戰,很多人都知道,有連篇累牘的研究,2020年甚至是歷史小說暢銷榜第一名。」
另一個例子,是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因火山爆發,當年歐洲成了無夏之年,非常冷,這件事被英國詩人雪萊記在了他的詩裏。同一時刻,北美的波士頓6月下了一場大雪。在中國雲南,那一年天氣特別寒冷,糧食歉收,造成了大饑荒。」葛兆光延伸闡述:「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跟氣候變化有關,因氣候造成糧食歉收,農民生存困難,法國大革命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葛兆光認為,明清的王朝更替也有類似原因。「為什麼李自成在陝北造反?陝北靠近內蒙,當時鼠疫橫行,同時氣候變化,糧食歉收,陝北出現了饑荒,流民多起來後,開始社會動盪。政府不得不從江南大規模運糧食,南方也怨聲載道,可糧食還是不夠,再加上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整個國家很快被掏空了。滿族軍隊就從東北打了進來。」
「全球歷史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全球史的研究視角,給歷史研究帶來了大變化,我越來越多地感到:全球史是重新認識世界、也是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個很好方式。」葛兆光說道。
香港史不能只談香港
既然是談全球史,訪問地又在香港,葛兆光當然必不可少地談到了東南亞以及香港史的研究情況。
他介紹了兩本「說文學不像文學,說歷史不像歷史,說隨筆不像隨筆」的著作。這兩本書均以東南亞為描述背景,近年在內地出版並引起反響。一本是馬來西亞學者莫家浩的《臆造南洋:馬來半島的神鬼人獸》,這位一路就讀暨南大學、北大、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學博士,以豐富的敘事細節展現華人在南洋的生活軌跡和文化認同,為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審視長期為傳統中國文化所忽視的馬華脈絡的跨域視野。
另一本《安南想像:交趾地方的奇跡、異物、幽靈和古怪》,是古典文獻學博士朱琺的小說集,作者基於多年前在越南的訪學經歷,結合自身對域外漢文文獻的研究,以古代對越南的舊稱「安南」「交趾」為背景,書寫了29種古代南方異聞,涵蓋奇跡、異物與幽靈等主題,在拼貼歷史碎片的同時,還暗含現代人的情感線索。
在葛兆光看來,這兩本流行著作在內地的爆紅,正因應了產能過剩下中國製造出海、中國已越來越深融入世界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對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全球化的好奇和想像。
針對香港和香港史研究,葛兆光則談了三點看法:第一,香港在聯接東西方、港澳台地區文化交流的中轉站作用。他以此次書展邀請龍應台演講為例,「香港就變成了一個所有地區、國家的學者,都可以交流的地方。」二是香港在海洋文明中的作用。「香港雖然是一個離島,但非常重要。因為15、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後,海洋已取代陸地,成為全球貿易往來的最重要通道。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才能意識到香港的重要性。」
葛兆光認為,澳門和香港是中國最早面向海洋的地方。「如時間線再長一點,明清時代的東南沿海一帶移民,是從泉州、漳州、廣州等地一路出去的。所以香港的意義,不在於香港本身,而在於是此前的全球殖民,以及現在的全球貿易、全球移民、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個動力。談香港史有點像談日本史,因為日本跟西邊的亞洲大陸連得太緊,講日本史時一定會講到朝鮮,講到中國。香港也同樣如此,就香港談香港,不會有太多東西,但就香港史談到殖民史、移民史、貿易史,講到它跟海洋、跟東海南海以及更遠的印度洋甚至歐洲的聯繫時,它就有意義了。」
最近,95歲高齡的歷史學家王賡武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新作《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葛兆光認為:「王賡武先生在東南亞出生長大,比內地人更敏感地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再強調中國應該重視海洋。我們也重視海洋,但從哪裏重視起?這樣香港就無法迴避。」
至於第三,則是研究香港史的多重視角。「現在有個趨勢,就是全球思想史或者叫大國思想史中,比較思想史的研究,越來越重要,我覺得從思想史的角度講,香港是現當代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1980年代後,香港對整個中國內地有很大影響。開玩笑說,那時的港普也變成了流行的時髦話語,它緊跟着就會對1980年代中國內地的思想轉化,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葛兆光認為:「現在學者們建議的學術研究重心,比如說跨國史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制度和文化認同的區分,以及華僑移民史,包括涵蓋了東南亞的華語文學等,都跟香港有一定關係。所以只要有一些觀念改變,把香港史納入更大的視野範疇,香港史研究會有很大變化。」
不知不覺間,這位名家娓娓道來的近一小時學術「龍門陣」時間已過。早年學術界曾有「有思想的學術」還是「有學術的思想」的議論,李澤厚則有「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無奈斷語。一位盛年已意氣風發、風華綻現,卻甘於長期埋首於故紙堆、以類似乾嘉學派的考據鈎沉功夫,沉穩度過學術人生的學者,回首人生時,是否有過一絲遺憾與不捨?睿智如葛教授,面對記者的多個提問,也只能以蜻蜓點水式回覆和迴避來禮貌結束。
不過,當他以綿密的思維、清晰的表達,呈現出知識、學術背後暗藏的思想鋒芒時,讓人不禁想起晚年王元化先生的看法:不可想像,沒有以學術為內容的思想,將成為怎樣一種思想;而沒有思想的學術,這種學術又有什麼價值?也許,這正是葛兆光經年累月治學所得的意義吧。行筆至此,一個念頭突然跳了出來: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著稱的滬上名學者朱學勤教授,多久沒來香港了。
(來源:香港文匯報B04:讀書人 2025/08/12)


























 字號:
字號: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