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小說創作歷程 馬伯庸:我在香港文化中長大

(大公報記者 顏琨、實習記者聶溥)香港書展期間,馬伯庸的「小說與中國近代醫事傳奇」講座備受關注,是書展首個三千人場的講座。從《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到《大醫》,「文字鬼才」馬伯庸的作品足跡出現在歷史的不同節點,而這是他的有意為之。「我想不斷拓展舒適圈,新的題材、新的領域、新的時代會給自己新鮮感,才能保持創作熱情」。《大公報》在今次香港書展上專訪馬伯庸,他表示自己「在香港文化中長大」,並從小說創作的經驗談起,講述歷史題材的創作歷程及首次嘗試編劇的身份新體驗。
藉着書展的邀約,馬伯庸來到香港,與讀者見面。「我之前沒有特別的和香港讀者有過交流,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內地,所以我想知道香港的朋友看過之後會有怎樣的感受和想法,我很期待這一次的交流。」

「遙遠的親切感」
對他而言,香港是一個有着「遙遠的親切感」的城市。「我在香港文化中長大,喜歡看金庸的小說;粵語歌的話喜歡聽溫拿樂隊、聽Beyond;電視劇喜歡TVB、亞視(製作的),還喜歡香港導演拍的電影。儘管從來沒有過在香港常住的經歷,但來到這裏,看着這些地名,就會有很多和童年回憶相關的記憶。」
每每到訪一個城市,都會給馬伯庸一些創作靈感,香港亦是如此。「香港本身有很多有意思的題材,比如九龍城寨、宋皇臺,甚至是一些史前的石刻遺跡。當然,像舞火龍這樣的民俗也很值得挖掘。」
從事歷史題材的創作,源遠流長的歷史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是取之不盡的靈感寶庫,「寫不過來」是馬伯庸的常態。自17年前的《風起隴西》開始,馬伯庸推出一系列歷史題材作品,口碑良好構成極具改編潛力的IP。《長安十二時辰》《長安的荔枝》推出後,馬伯庸筆下的古代「打工人」獲得不少讀者的共鳴,這離不開他10年上班族的生活經歷。「作家很難超越自己的生活經驗去創作,我會不由自主地去寫一些『社畜』的故事。」《長安的荔枝》裏,主人公李善德是唐代「房奴」,陰差陽錯成為了那個運荔枝的「倒霉蛋」。
創作靈感是經由平日的觀察中厚積薄發而來。馬伯庸秉持着「趕上什麼展就跑去看看」的隨緣心態前往博物館。在他看來,展覽將古代文化集中展示,將一個線頭展現出來。順着線頭向下深挖就能有不少收穫。
回憶起不久前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的經歷,馬伯庸對一個測深錘留下深刻印象。「這是古人用來測量水深的,但我看到的細節是,古人會在鉛錘的底部塗一圈牛油,這樣就可以黏住水底的沙粒,從而判斷海底的地質條件。」那個名為測深錘的展品就是一個線頭,將馬伯庸帶領到特定領域的歷史海洋中。「我把整個從古至今的鉛錘形態、古人的技術以及為什麼古人要判斷船底的地質條件,為了應對這種地質條件他們下錨時要怎麼做,適合遠洋和近海的船隻特點,都了解了一下。」
從舊報中觀察時代
新作《大醫》則是因為在上海華山醫院做講座而萌生的。在籌備的4年間,他進行大量的資料考證,甚至為了創作多次前往醫院與醫生交流。 「《大醫》是我第一次寫80萬字、時間跨度近半世紀的作品。我寫完這本書之後,對歷史的理解,對大事件背後的動因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在創作《大醫》期間,馬伯庸查閱了自清末到民國時期的《申報》。「我每天大概要看兩到三個月的報紙,把老報紙看一圈才能體會到當時的時代質感。」
在看老報紙的時候,馬伯庸會尤其留意廣告。「廣告其實是最符合當時時代的『網紅語言』,當時最流行什麼樣的詞、最喜歡什麼樣的表達方式、他們如何去誇張的吸引大家來買東西,這些都是極能反映時代風貌的內容。」他曾觀察到,清末時期流行的廣告語是「西洋大醫師精心炮製」,而到了1920年代就忽然變成了「東洋大醫師」,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入侵以及日本經濟的崛起。
對馬伯庸來說,寫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每寫完一部作品對歷史的理解就更深一層。閱讀資料、前往不同地區采風讓他持續發現好的創作切口。「有的時候我也會搞不清楚是為了寫作而去閱讀,還是為了能讀更多資料來寫作,當然這種搞不清楚也很開心。」目前,靜靜躺在他電腦文件夾中的「創作靈感」就有20多個。
新作分享|《食南之徒》:「吃貨」視角撬動歷史版圖
在香港書展的講座上,不少讀者對馬伯庸的新作頗為好奇。馬伯庸對新作《食南之徒》的描述則是,這是一個廣東「吃貨」的故事,這個不一般的「吃貨」推動了西漢初年版圖的變化。馬伯庸喜愛美食,儘管古代的很多美食其實並非像想像中的那般滋味,但他在查閱歷史資料的過程中仍會多看一眼和食物相關的內容。不下廚的他亦會有復刻古代美食的幾次經歷。
「我曾嘗試復刻過宋代出現的『蟹釀橙』,把一顆橙子剖開、挖空後,把蟹腿、蟹肉和蟹黃分成三層放在橙子裏。然後把這個橙子一整個放在鍋裏去蒸,蒸熟後撒上一點鹽來吃。這道菜並不是用強烈的味覺來刺激你,而是要你在很悠閒的狀態下去細細品味。我覺得這種吃法很精細,非常具有文人風。」
在新作《食南之徒》中,馬伯庸曾在社交媒體上與網友分享用ChatGPT繪製主人公唐蒙形象圖的感受。在他看來,AI為人類展現出了一種可能性。「AI很像貓,是有智慧的生物,但是卻不聽你的。所以需要反覆的調校、反覆提要求,才能勉強接近你想要的效果。」
身份切換|作品獨立 不成「宇宙」
《長安的荔枝》和《大醫》一經推出便受到視頻平台的關注,在極短時間內相繼宣布IP影視化。再加上此前改編的劇集頗受好評,給不少觀眾留下「馬伯庸宇宙」的印象。
但馬伯庸自己卻很害怕用「宇宙」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作品。「宇宙意味着彼此之間有聯繫,但我一直盡量讓我的作品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獨立的,這算是我個人的執念。」

除了作家的身份,馬伯庸亦體驗了一次編劇的生活。年初和觀眾見面的劇集《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是馬伯庸首次擔任編劇的作品,這讓他感受到作家和編劇之間的差距,文學表達和視聽語言之間有時無法等量置換。在這次書展講座上,他還以「馬伯庸出現在書展講座」為情境為觀眾演示兩者的不同。而回憶起這次編劇經歷,馬伯庸笑言,「未來暫時不會主動做編劇,我覺得客串一次就夠了。」

創作經驗|向太太請教女性角色寫法
馬伯庸談到正因自己不太擅長描寫女性,所以自己筆下最滿意的女性角色其實是《長安的荔枝》中男主角的夫人,雖然戲分不多。他笑稱自己年紀大了,對描述老夫老妻的情節還挺游刃有餘的。而在描寫女性角色上,他說多虧太太給予他寶貴的經驗。
「實話實說,我寫女性角色之前經常被吐槽。大概是在創作《兩京十五日》之前,我太太告訴我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將這個角色當做一個獨立角色來寫。把角色的想法、立場、動機寫清楚,她不依附別的角色,而是有自己的獨立選擇。只要角色寫出來了,她恰好是女性就好了。」在那之後,令人驚喜的是,馬伯庸筆下的女性角色鮮活生動了不少。
(來源:大公報A7:文化 2023/0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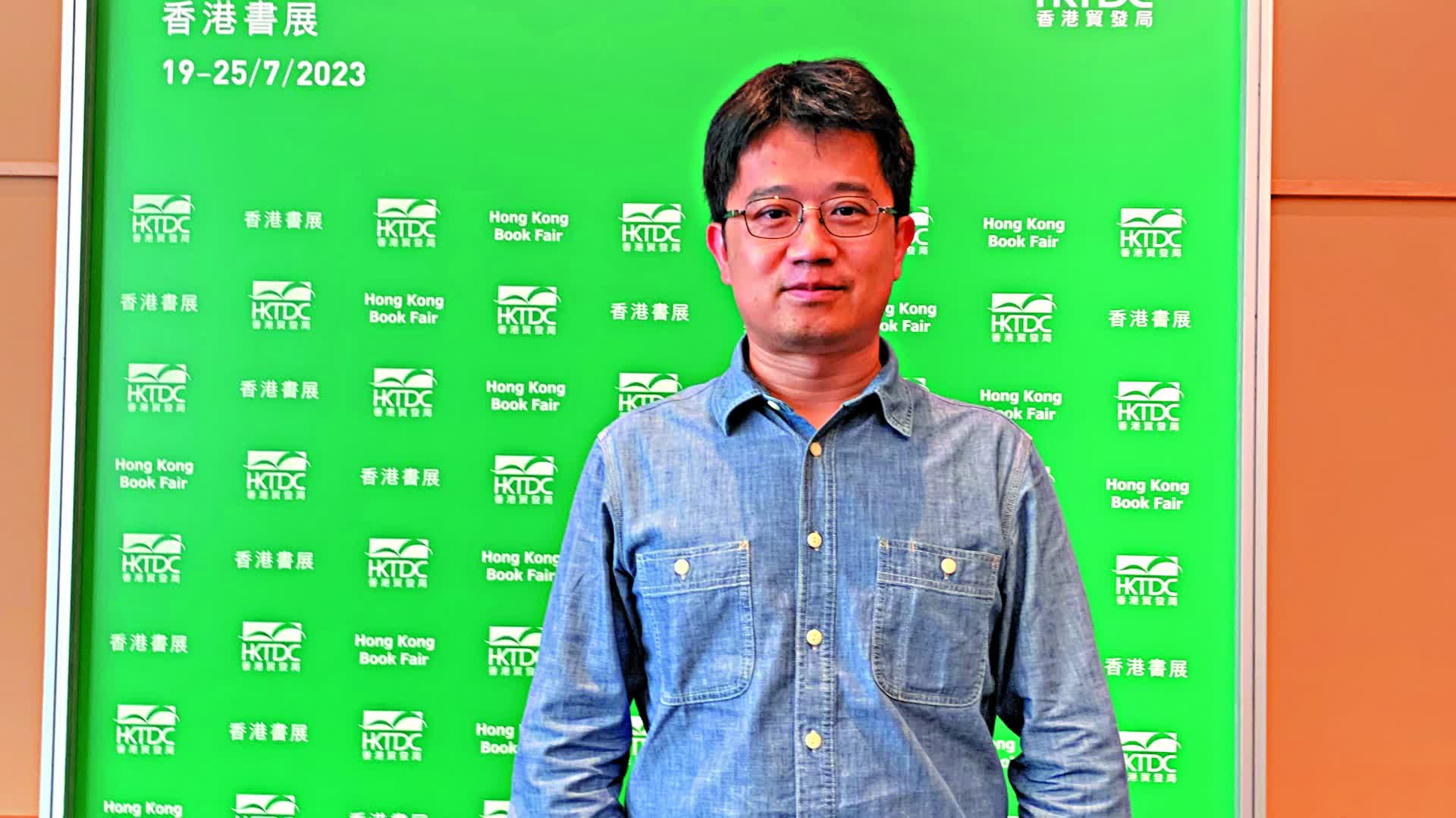

























 字號:
字號:


評論